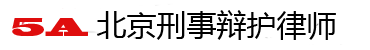发布时间:2018-12-16 22:08:41 信息来源:5Aob欧宝体育富网入口刑事欧宝全站官网登录网
从何时开始可算犯罪

——从隐藏、转移或恶意毁损、转让财产切入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简称拒执罪)的行为起始日究竟应当怎么界定,这是一个尚有争议且亟待明确的现实问题。法学理论界对此尚缺深入的探讨研究,论者们囿于相关司法解释和立法解释的字面表述,一般是纠结在从执行申请抑或执行通知发出起算之上。也有一些论者主张以裁判生效之日为拒执罪行为起算日,有的甚至认为裁判生效之前的预拒执行为也应纳入拒执罪行为之列,然而其论证尚难令人信服。而司法实践目前则处于各行其是的状况,有的从执行程序开始后起算,有的则起算于裁判生效之时。最高法院近日对拒执罪做出最新的司法解释,解决了追究拒执罪的实体和程序的重要问题,遗憾的是对于拒执罪行为的起始日问题却未有明确而直接的回应。本文的基本看法是:拒执罪行为有的只能在执行程序中发生,比如属于“硬拒型”的使用暴力等对抗执行的行为;有的则可能在法院裁判生效之后即发生,最为典型的是属于“软拒型”的隐藏、转移或恶意毁损、转让可供执行的财产;至于诉中乃至诉前的预拒执行为,在有权机关未明确作出入罪表态时不宜纳入拒执罪。下面从隐藏、转移或恶意毁损、转让财产切入,围绕拒执罪行为起始日的界定这一主题展开分析论证。
认为拒执罪行为起始日应以执行通知发出为标志的依据,是最高法院《关于审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项规定。该项规定将“在人民法院发出执行通知以后,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已被依法查封、扣押或者已被清点并责令其保管的财产,转移已被冻结的财产,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作为拒执行为“情节严重”的情形之一。仅从该项规定来看,确实有“发出执行通知以后”的时间限定,似乎可以作为支持“执行通知说”的依据。然而,该第三条规定了六项,第六项是个兜底条款:“其他妨害或者抗拒执行造成严重后果的。”既然有这一兜底条款,那么裁判生效之后执行通知发出之前隐藏、转移或恶意毁损、转让财产,造成无法执行的数额巨大的拒执行为也是可以被包含在其内的。可见,仅就“法释解释”来看,“执行通知说”就存在可商榷之处。易言之,不可以仅仅基于该第一项规定而进行反面解释,进而推出拒执罪行为的起始日都应以执行通知发出为标志。更何况,“执行通知说”并没有得到全国人大常委会之后作出的《关于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的解释》这一立法解释的支持。
上述立法解释规定了五项拒执罪行为,与“法释解释”第三条第一项相对应的情形被表述为:“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这里的改变主要有二:一是隐藏、转移或恶意毁损、转让财产不限于已被依法查封、扣押、冻结或者已被清点并责令其保管的财产;二是拒执罪的该类行为起始点不受“发出执行通知”的限制。这说明,拒执罪的此类行为不再限于“执行通知发出”之后。然而,由于其中用了“被执行人”这一概念,于是就有拒执罪的该类行为应以申请执行为前提的“申请执行说”。该说的理由为“被执行人是相对于申请执行人而言的一个法律概念,无申请执行人自然也无被执行人。”依笔者看来,“申请执行说”也是难以自圆其说的。一是根据民诉法第二百三十六条规定,执行有申请执行与移送执行两种,后者的被执行人就不与申请执行人孪生。二是该立法解释规定了五项拒执情节严重的情形,第五项也是兜底条款。因此,与其说根据“被执行人”用语推出“执行申请说”,不如将拒执罪主体解释为“负有执行义务的人”,而负有执行义务的人是包括生效裁判确定的给付义务人的。
再者,界定隐藏、转移或恶意毁损、转让财产类的拒执罪行为的起始日,还需要通过刑法规定拒执罪的犯罪对象的考察,挖掘蕴含其中的法理加以论证。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规定的拒执罪罪状为:“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拒执罪的犯罪对象是法院的判决、裁定,而用以执行的裁判自然是已经生效的裁判。也就是说,拒执罪行为是针对生效裁判的,所挑战或对抗、侵犯的是生效裁判的权威这一客体,而不仅仅是针对法院执行行为、对抗法院执行权威。因此,只要是违反生效裁判确定的给付义务,都构成对生效裁判权威的挑战;只要有能力履行生效裁判确定的给付义务,而拒不履行该义务并且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都成立拒执罪。而法院裁判生效之后申请执行或移送执行之前,负有执行义务的人隐藏、转移或恶意毁损、转让财产,仍然可以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比如由于隐藏、转移或恶意毁损、转让财产,造成无法执行的数额巨大甚至特别巨大,这无疑是可以纳入立法解释关于拒执罪行为情节严重的其他情形的,“法释16号解释”第二条第八项将拒执行为“致使债权人遭受重大损失”纳入拒执罪便是个明证。
既然拒执罪的犯罪对象是法院生效裁判,那么就再来看看生效裁判是怎么确定履行裁判确定给付义务的时间?判决书确定履行时间的表述通常是:“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有的为十五日内)……”。其中清楚地写明是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也就表明负有给付义务的人对判决的履行义务起始日是判决生效之日。虽然按照民诉法第二百四十条的规定,执行员接到申请执行书或者移交执行书后还应当向被执行人发出执行通知,再次指定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给付义务的期限,但那是在给付义务人未自行履行给付义务之后给个自行履行的宽限期而已,绝不是更改生效判决所确定的履行给付义务的起始日。因此,给付义务人履行给付义务的起始日仍是判决生效之日。如此,义务履行起始之后以隐藏、转移或恶意毁损、转让财产等方式拒不履行义务,也就成立拒不执行判决行为,情节严重的应当构成拒执罪。与判决生效之后还给负有执行义务的人自动履行期及其宽限期不同,执行方面的裁定不论是先予执行等的诉中裁定还是执行生效判决的判后裁定,一般是裁定一经送达即生效、一经生效就执行的,因而对生效裁定的拒执罪行为从裁定生效之日起算是不言自明的。
至于诉中乃至诉前的预拒执行为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即致使之后的生效裁判“无法执行”或者债权人遭受“重大损失”的,可不可以将其作为拒执罪予以刑事追究,也就是拒执罪行为的起始日可否前移到诉前行为日或案件起诉日的问题,确实很有必要予以进一步斟酌。如果说为了逃避债务履行而在诉前隐藏、转移或恶意毁损、转让财产,债权人有着法律途径加以救济,即依照合同法相关规定提起确认合同无效诉讼或者行使撤销权(甚至依照刑法追究债务人诈骗罪的刑事责任),拒执罪大可不必介入的话,那么案件起诉后的诉中预拒执行为呢?只将情节严重的诉中预拒执行为作为妨碍民事诉讼行为而对行为人采取罚款、拘留强制措施,债权人的损失仍然难以得到有效救济。从解释学的角度来看,拒执罪的“拒不执行”的平义虽可理解为现实而直接针对既有生效裁判的拒不执行,但也可根据“执行难”的实际情况进行共时解释,使其扩大到预先而间接针对将来生效裁判的拒不执行。不过话虽如此,本文还是倾向于持相对保守的观点,即在有权机关未明确对“拒不执行”作出扩大解释时,还是以平义理解“拒不执行”为宜,不将裁判生效之前情节严重的预拒执行为纳入拒执罪行为。
以上主要就隐藏、转移或恶意毁损、转让财产之类的“软拒型”的拒执罪探讨其行为起始日,而拒执罪行为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所以,还需要对拒执罪的立法解释和新司法解释规定的拒执罪行为进行分类而加以整体把握,分别界定其行为起始日。该两解释规定的情节严重能够构成拒执罪的拒执行为,根据其行为可能发生的时间可以区分为两类:一类是在裁判生效之后执行程序启动之前和执行程序中均可能发生的拒执行为,另一类是只能在执行程序中发生的拒执行为。前者包括立法解释中拒执情节严重的(一)、(二)情形,以及新司法解释第二条规定的(八)情形;后者则包括立法解释中的(三)、(四)情形,以及新司法解释第第二条的(一)、(二)、(三)、(四)、(五)、(六)、(七)情形。前一类拒执罪行为如上所述应以裁判生效之日为其起始日,而不论实际拒执行为发生在裁判生效之后还是申请执行之后;后一类拒执罪行为的起始日执行程序启动之日。这里还需要说明的是,这里之所以将立法解释中的(二)情形列入前一类拒执行为,是因为其中的“已向人民法院提供担保的财产”,既可能是为解除财产保全而提供的诉中担保的财产,还可能是执行程序中提供担保的财产。
请添加本欧宝全站官网登录团队微信号: